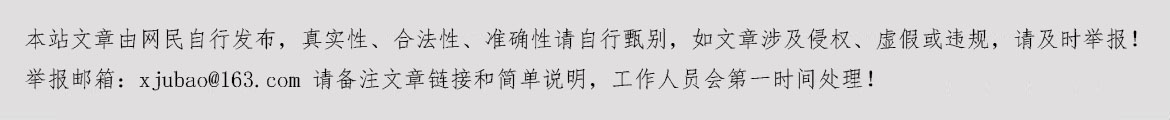近期,多个知名药企先后传出裁掉销售团队的消息。曾经风光无限的“医药代表”,目前正面临裁员、调整和转型阵痛。在业内人士看来,超过300万医药代表纷纷“退场”的背后,是医药行业的风云巨变。
黄金时代医院欢迎医药代表去宣讲
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
在那个缺医少药和信息匮乏的年代,医药代表们带着外国“新药”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是医生了解医学前沿的宝贵渠道。与此同时,从1985年开始,无锡的华瑞、上海的施贵宝、西安杨森和天津的中美史克这些最先成立的合资企业纷纷开始开辟中国市场,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该怎么“卖药”?当时的中国,拥有高度集中的医药购销渠道,中国的制药企业是按计划完成生产量,再由各地医药公司收购,统一调配至各地医院、卫生院。严密的计划体制下,中国的药企不对终端市场直销,也就不需要销售部门。但这些合资药企的产品一“生下来”就没人收购,必须自己卖。
在制药行业,西安杨森一直以完备的内部培训体系和职业成长计划而为人称道,有业内的“黄埔军校”之称。20世纪90年代,西安杨森制定的营销推广方式有“推”和“拉”两种。“推”是通过当地商业公司介绍,邀请医生参加学术推广会,一场会结束,往往能签下许多订单。而“拉”,则是医药代表直接去医院拜访介绍,也便是沿用至今的医药代表的主要工作方式——“专家拜访”。
关平(化名)辞职去西安杨森做医药代表前,曾是西安理工大学的辅导员,一个有干部编制、让全家脸上有光的铁饭碗。但在学校720元和药企1万元的年薪面前,关平毅然扔掉了铁饭碗。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拜访医生的经历,“从当地最大的医院开始,进门就问人药剂科的位置——一般都在医院最阴暗的犄角旮旯里头”。见到穿着工整的中外合资企业白领上门,药剂科主任热情地请关平坐下,还主动带他去见消化内科主任。不到2小时,关平拜访了5个科室,拿下当地4家医院的单子。关平还记得,一位主任医师在听完他的介绍后,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说:“干了这么多年的医生,从来没人跟我说过产品该怎么用,你是第一个。”
与关平同时期入职的另一位初代医药代表则回忆,当时他们西装革履,拎着投影仪、开着桑塔纳轿车来到各个市县,常常是地方卫生部门的一把手、医院院长亲自到门口迎接,医院门口有时还会挂着“欢迎某某公司宣讲”的横幅。甚至有科室主任听完课后,会给医药代表递上信封,里面塞着讲课费。
对医药代表而言,那是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
失序竞争带金销售逐渐成主流操作
以“新药”打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批外国药企,起初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但从1993年左右起,关平发现,药品库存明显下降得慢了,出入医院时会频繁见到陌生的同行面孔——他们不再是医院里的唯一的一群医药代表。
1992年后,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全国各地卷起承包老药厂、开办新药厂的风潮,外资药企同时涌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自由造就了新的医药市场竞争局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医药代表营销——医药代表实务》一书显示,1990年至1996年,中国的医药品消费一直保持着年均15%至2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物价上涨指数的3至5倍,也远高于GDP的同期增速。
所以,1994年国家提出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1997年,医药消费增长过速的势头被有效遏制。这是医药代表们第一次受到大环境与政策的冲击。当时,各地都有大量的药企药厂,在没有民营医院和药房的情况下,药品销售的渠道只有公立医院。为了保证自己的销售业绩,2000年前后,“带金销售”的手段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
风云突变医药代表面临大“围剿”
即便如此,2009年新医改全面展开之前依旧称得上是医药代表的“掘金年代”。直到2009年新医改启动,在药品零差价、重点监控目录等方面狠招频出,一点点斩断了药品利润空间,医药代表的日子开始真正变得不好过了。
这几年,医药行业更是迎来了风云巨变,其中最大的两项改变是“两票制”和“带量采购”的落地。2017年1月11日,国务院医改办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提出逐步推行“两票制”。“两票制”是指在药品从药厂流通到医院的过程中,只能开两次发票: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并且每个品种的一级经销商不得超过两个。随着“两票制”的执行,药品的流通环节被大大压缩。
2018年11月,《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发布,国家在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试点集中采购。实际上,“带量采购”相当于国家主导下的大规模药品“团购”,目的在于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截至目前,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实施了五批,城市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20多个省份,平均降价幅度在50%以上,有些药品的降价幅度甚至在90%以上。业内认为,在此背景下,300多万医药代表将面临大“围剿”局面,“尤其是在带量采购这场雪崩中,医药代表无疑会是先被埋没的群体”。据悉,自2018年12月首批4+7“带量采购”药品名单公布以来,医药行业内至少有40%的医药代表已经离职。
另外,针对医药代表,也有相应的新规出台。2020年12月1日正式执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医药代表不能有以下行为:未经备案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未经医疗机构同意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这也意味着,此前医药代表主要承担的销售职能被明令禁止。
很多从业者开始认为,很多药厂已不需要医药代表。即便剩下的医药代表,也开始转做药品的投标、发货、配送跟踪等工作。
专家观点倒逼医药行业走向正规化
在国家集采和价格谈判背景下,无论是仿制药还是创新药,利润空间进一步减少,使得市场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带金销售等医药行业不正当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府还鼓励企业员工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给予重奖。2020年9月初,安徽多家三甲医院贴出了匿名举报信。举报信直指,这些医院部分科室(外科+内科)医生和医药代表存在带金销售问题。随后,山西临汾市人民医院也出现了举报信。在行风建设趋严,大批院长、主任纷纷“落马”的情况下,关于医药代表贿赂的举报信频频出现,给医院造成了巨大压力。很多医院纷纷约谈医药代表,召开廉洁会议。
目前,虽然医药代表处于艰难的转型期,不过,有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表示,这个职业不会消失,未来一定是走向正规化。
“从这个层面来讲,这未尝不是倒逼医药行业走向正规化的一次进步。在带量采购、医保结余奖励等背景下,医药营销规则已经在逐渐改变。未来医药代表将回归其本质,不再背销售任务,而是做纯学术推广。因为很多专家仍需要对产品的特性、治疗方案等进行了解。”北京鼎臣医药管理中心负责人史立臣指出。
一则爆料,把医药代表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传信息显示:8月10日上午,某港股上市生物制药企业工作人员吴某复制了医院进修医生的个人门禁卡,从职工通道入院,一路进到门诊、病房等区域,直至被保安截获。
这已不是吴某首次违规拜访。该院保卫科回溯发现,8月6日,吴某就持门禁卡进入医院。10日截获吴某后,保卫科没收了门禁卡,并向医院纪委办公室、药学部、教务处通报。
8月25日,该网传企业公布2021上半年业绩,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8.54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9.2亿元,增长101%。
同时,大幅上涨的销售费用,让亏损幅度同比增长了近1倍。
药代吴某违规入院,或许是激进销售策略之下的一个注脚。
销售队伍大扩张,违规事件难以完全规避
该企业半年报显示,公司收入同比翻番,官方解释这得益于“达攸同”、“苏立信”、“达伯华”以及“达伯坦”四款新药的优异表现。
这几款药物分别是生物类似药贝伐珠单抗、阿达木单抗、利妥昔单抗,以及从Incyte公司引进的培美替尼。
但外界更关注的,是另一品种——
根据合作方的口径计算,该生物制药企业的PD-1产品“达伯舒”2021年上半年收入约为13.9亿元。
相比百济神州今年上半年PD-1收入的8亿元,这个成绩显然更胜一筹。
总营收屡创新高的背后,是销售费用的快速增长。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的“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是11.37亿元;去年同期这一开支仅为4.46亿元。
截至2021年8月31日,国内已有信达、恒瑞、百济、君实、康方以及誉衡六款国产PD-1获批上市,另有4款进口PD-1/L1。在中国,PD-1市场已进入跑马圈地的关键时刻,稍有松懈就会功亏一篑。
该公司正在持续扩充人手。财报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就新入职了1300名员工,目前全公司负责商业化的销售人员有2100名。
销售团队人数激增,考验着团队的管理能力。巨大的业绩压力之下,一线药代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都不足为奇。
但是,不论复制门禁卡难不难,药代和管理者都不能忘记:合规是底线,越线就会产生风险。
卫健委掀反腐风暴,药代今后谨遵底线
前述消息显示,该医院除了没收吴某的门禁卡,还通知了他的主管,核实吴某的工作单位情况。同时,因为吴某无法提供7天内的核酸证明,该院对药企违反来访人员管理规定,给医院防疫工作带来风险的错误,也提出严厉批评。
目前信息显示,这仅是内部通报,院方尚没有对这家药企做进一步处罚。
2020年12月实施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未经医疗机构同意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
医药代表的拜访,已经成为监督医药反腐的重要一环。国家医保局将“带金销售”纳入征信体系,与药械招标采购挂钩,如果医药代表行贿,涉事企业将面临失去市场和巨额罚款的风险。
今年8月初,国家卫健委印发通知称,自2021年至2024年,集中开展整治“红包”、回扣专项行动,对涉嫌利益输送的各类机构,严肃惩处、移送线索、行业禁入,持续保持对“红包”、回扣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医药代表不惜顶风冒险,复制门禁卡违规入院“拜访”,在政策密集出台的时候,显得十分突兀。
卫健委对接下来3年的“整治红包”行动,尚未出台明确的处罚措施。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合规压力升级,市场游戏规则巨变之下,医药代表工作的调整只会更加密集。
医药代表的转型是对中国医药产业的一次大考,不论政策变化还是创新药的加速上市,都在迫使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本位。
来源:米墨药事官